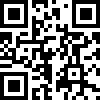在刚刚过去的20 世纪,科学的进步和物质文明的发展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给人们的生活和工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效率和便利;同时,西方工业现代化伴随的消极后果也逐渐显露,生物物种加速灭绝和生态环境的急剧恶化,使“先发展后治理”的工业发展模式遭到了普遍质疑。加上两次世界大战及世界范围内的道德危机,20 世纪展示了一幅复杂的图像。新世纪的开始,人们意识到建立物质与精神的平衡势在必行,东方传统文化的价值凸现了出来,以缘起思想为特征的佛教文化精神显出了特殊的意义。
大乘佛教的缘起思想:
大乘佛教思想纷纭庞杂,但离不开一个核心,就是缘起思想。缘起思想认为一切有为诸法,也就是现象界的万事万物,皆因缘和合而生。它有几个特点:
第一,缘起的本质是和合性。佛教认为,事物生起的原因是因与缘的和合;同样,事物的存在亦是因与缘凑合的结果。也就是说,事物完全系属于因缘,依赖于各种条件的具备与会合。这排除了全能、超因果、永恒的造物主的存在,也否定了块然自生的可能。在因与缘和合的关系中,因、缘虽有主次之分,但二者都不可缺少。因是一,而缘却有众多。因对事物的产生及性质的限定起主要作用,缘起辅助作用。
第二,缘起具有变化性,即所谓无常性。佛教认为,事物的存在仅是一种暂存。现象的这种暂合性或暂存性,被称为无常。佛教用生、住、异、灭四相来描述,大乘佛教更将无常性解释为刹那生灭。一切事物(包括生命)都处于刹那生灭变化的过程中,是一种永恒变动之流。这样,一切事物,由因缘和合而成,前灭后生,相似相续,无有止息。
第三,缘起具有时间和空间的普遍性。佛教认为,缘起是一切时空的一切现象所遵循的法则。不管是现在,还是过去与将来,一切事物莫不如此。换言之,在任何时间、空间,任何事物都不可能是恒常的,不可能自然而然地生起,不可能从惟一因或不变之因得生,亦不可能由神创生,更不是无中生有,必须是因与缘合会,即各种条件凑泊,才得生起及存在。
第四,缘起具有彻底性。佛教认为在这种因果关系中,一方面,一一物作为果,同时亦是因(或缘);另一方面,一一物作为因(或缘),同时亦是果。即一切物既是果,也是因(或缘);既是因(或缘),也是果。万物彼此互为因缘,相依而生。
第五,缘起具有整体性。佛教的彻底的因果思想表明,一切事物处于一种整体的因果连摄中。一物通过因和缘的“纽带”,联系其他事物;其他事物亦通过因与缘的“纽带”合会于此物。这样,一切事物就相互联系,互为因果。太虚曾有一非常恰当的说明:“我人的一举手一投足,语默动静,无一不与万事万物为缘而互通消息;更推广论之,山间的一草一木,海洋中的波涛与空气,天上的星球运作,无不与每一物互相为缘以致其违顺消长。”大乘佛教缘起思想的文化精神特质。
人类的生命体悟和实践历程,表明了个人、社会、自然间相依相生的一体关系,大乘佛教的彻底的缘起思想深刻地把握了这种关系。以这种缘起思想来观照人与社会、自然界之间的关系,就揭示出大乘佛教的文化精神,这是一种新的文化透视观。
按照缘起思想,佛教谈人与自然界、社会的关系,有三个层次。首先涉及的对象是一切事物的全体即宇宙,它含摄一切事物,不论是生命(包括人)还是非生命体,这也可称为自然界;其次是生命界,指一切生命;最后是人类社会。当用佛教的缘起观去观照这三个层次时,就产生了佛教的文化精神,可以概括为四点:一体平等,相生共存,同感亲和,自利利他。
第一,相对于宇宙全体,缘起观提倡一种一体平等的精神。在缘起观的观照下,森然万象虽然形形色色,变动不居,但一体相连。一体的万物彼此相缘,又各有自位。从缘起的角度看,任一物都不能凸现出特殊的重要性,任一物在余物的缘起中都不可替代,不可或缺。在一体平等精神的观照中,宇宙万象前灭后生故生生不息,刹那不住故活泼新奇,因缘所生故平等一味,相互涉入故和谐共处。人、动物、植物乃至一切生命、非生命体,皆一体平等,和谐无碍。这是大乘佛教缘起思想的文化精神的第一层含义,也是其最基本的含义。
第二,缘起观揭示了一种相生共存的文化精神。在普遍的缘起关系中,每一事物都依因缘和合而生,由因缘和合而生,则无有自性;由无有自性,则不能停住;由不能停住,则刹那生灭。刹那生灭的万物,本没有相续的存在,但由因缘力,能前后相似。刹那前后相似的事物,在人的眼中,就是一个相续的东西。由此,事物就获得了连续的存在。因缘和合而起即生,前后相似相续即存。
从生存和发展角度看,相生共存的一个重要例子是自然界中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其他事物的关系。人类与整个自然界的命运息息相关,相待而生,相待而存。人并没有优越于自然界其他生命或事物的特殊的生存地位。人的肉体需自然界的食物、阳光和空气,人的劳作休息需以大地为场所,人的情感需自然界的山水、草木、光色、声默、动息来滋润。人类和自然界消息感通,彼此相生共存,这既是二者生存的原则,也是二者发展的原则。
第三,当缘起思想观照包括人在内的一切生命所属的生命界时,同感亲和也是一种基本文化精神。佛教认为,一切生命之间不仅具有缘起和合性事物一体平等、相生共存的依存性,还具有由感受知觉能力带来的可沟通性。由此,人对生命界本能具有同感之心、悲悯之心。反映在文化精神上,就是同感亲和:与生命相感通,对生命生悲心。
第四,从人类社会的角度出发,缘起思想阐明了一种自利利他的精神。按照缘起的思想,人与万物相生共存,一体平等,是一种普遍恒存的“自然联系”。由于人具有情感与理智,即具有思想行为的特殊能力,人与人的相互影响,形成了自然物间所没有的“社会联系”。“社会联系”比“自然联系”更明显更紧密,对个人生存的制约性也更强,人直接地依赖于整个社会,反过来,个人的思想、行为对社会影响亦大。人的存在由“自然联系”与“社会联系”所决定,必定是“依他”的;人无法只通过自身而不借他人他物获得独立自足的存在,必定是“无我”的。依据此无我依他的生存本质观,对别人有害的行为,最终会有害于自身;反过来,利于别人的,最终会利于自身。一个真正道德的或者负责任的行为,必定是自利利他的。大乘佛教缘起思想的现实意义。
人类在其生命的历史长河中,从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出发,为了追求自己的短暂利益,经常忽视人、自然、社会的一体共生性,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使人类和自然界的生存前景蒙上了暗重的阴影。
18 世纪开始的工业革命,给西方发达国家带来了物质繁荣,带动了全球经济的发展。但是,人类却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生物种类的大量灭绝、环境的不可逆转的污染与破坏(江河断流、土地沙漠化、能源危机、臭氧层的破坏等),越来越沉重地压在人类的心头。人类如果再按惯性走下去,不仅物质文明只会昙花一现,人类的生存家园—地球也将提前报废。这说明,人类一味追求物质的繁荣是错误的,其结果必然是自掘坟墓。因此,必须放弃“先发展后治理”的经济发展模式。究其根源,此模式来自于西方文化中征服自然的“相克式”思想传统。这种思想传统设定了一个永恒的、无限的自然界,它同时扮演着两个角色,既是人类桀骜不驯的敌人,又是人类获取财富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这样,人类的任务就是劳其思虑地征服自然界、变本加厉地压榨自然界,使它在人类面前低头,乖乖地交出它所有的一切。殊不知,自然界是一个有限的、非永恒的存在,像人类一样脆弱。对自然界的破坏与掠夺,必然导致生命和自然生态的灾难,最终反作用于人类自身。
人类社会已经注意到上述生态危机的严重性,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思想。并开始关注人、社会、自然界“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整体关系,试图调整人类对待自然的方式。但是,如果不彻底抛弃“相克式”(“征服式”)的思维模式,人、社会、自然和谐发展的良性循环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首先要确立新的文化精神,以从根本上解除人类面临的生态危机及社会失衡,建立人、社会、自然的可持续发展的新型关系。这种新的文化精神,作为“相克式”(“征服式”)思维模式的对立物,应该昭示出,人类和自然界(包括生命界)都是有限存在。自然界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前提,也是人类快乐和幸福的源泉。毫无疑问,不可能有离开自然界的人类,同样不能想像离开人类的自然界,二者一体共存。人类应该亲近自然界,珍惜、爱护它的一草一木与每一生命,与它亲和相依、共同发展。而在享用自然界的财富时,不要掠夺、破坏、浪费,要保证其再生能力,维护自然界的生态平衡。同时,这种新的文化精神,还应告诉人们,人与人之间是相互依存的关系。他人不是与己断然不同的存在,实际就是以“他”的面目出现的自己,自他本是一体的。个人不可能离开社会而独存,必依赖于社会提供的生活与生产资料、信息,及需要社会的爱与安全的保证。社会也需要每个人负责任的参与与奉献。换言之,人须认识到他人的重要性,破除“自我”的壁垒,彼此间相互尊重、亲和友爱、自利利他,这样,自私与贪欲就能得到对治,从而建设一个和谐平衡、持续发展的社会。这种文化精神,可称为“相生式”(“亲和式”)文化精神。因此,人类社会与自然界能够持续发展的关键,是要在人类的意识形态和心灵中确立亲和相生的“相生式”(“亲和式”)文化精神,并以这种文化精神为基础,建设新的世界文化。
前面所述的大乘佛教文化的精神对建立“相生式”(“亲和式”)文化精神有独特的意义。首先,一体平等、相生共存的精神表明了万事万物的相互联系,即自然、人的一体性和平等性。只有珍惜、爱护自然界的每一生命个体和一草一木,与之相缘共存,人类才能生存与发展。其次,同感亲和的精神表明生命个体的平等性、一体性,及对生命的尊重、珍惜,对生命的感受与对苦难的同情。一体平等、相生共存、同感亲和的文化意识能够消解人类心理结构中的过度扩张与征服的冲动,逆转人类对自然界的强势压榨,建立人类和自然界的和谐同盟,使自然界的生命和事物重新焕发生机,成为人类的生命之源和精神家园。而以利他为先的自利利他精神能够对治人类的“唯我”情结,增强道德意识,关心全人类的精神和物质的福祉,使人类生活在一个安宁与和平的社会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