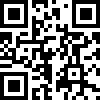龙天共护
龙天,是佛教中八部天龙和天神的统称,据说,在佛居住说法的地方,总有他们护持。
榆社地处太行山偏僻闭塞之地,与外界沟通接触的机会相对较少,但历史上的榆社,却“山山有寺,村村有佛。”直到解放初期,只有800多人口的榆社潭村尚存9座寺庙。
佛教在这里曾盛极一时。藏有佛祖真身舍利子的中国十九座舍利塔中的第十八座舍利塔,就建在榆社。
虽经岁月洗刷,抗日战争时期又被日军飞机轰炸了七十多架次,榆社依然幸运地保存了规格较高的寺院4处,其中两处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一处是金时的崇圣寺,一处是元代的福祥寺。
榆社有许多地名,包括村名都和佛教有着密切的关联。比如大寺圪垯、梁寺头、前寺沟、后寺沟、寺上、寺儿、寺家凹、庙岭、庙沟、焦红寺、榆林寺、金藏等等。
此外,榆社还有一座座无可计数的北魏、北齐及唐代的佛教石窟、石刻造像,如一枚枚散落的佛珠般,记录着有关佛教文化的遥远信息。
两个皇帝成就榆社佛教文化
榆社与佛教文化的渊源,始于两个人—两个皇帝。
一个是曾经在这里生活过的后赵皇帝石勒,一个是曾经经过这里的北魏孝文帝拓跋宏。
石勒本是羯族,信奉的是火祆教(又名祆教、拜火教)。但他在南征北战、烧杀抢掠的时候,遇到了一个人,西域高僧佛图澄。
西晋永泰四年(公元310年),80岁高龄的龟兹国人佛图澄抱着广建寺院、弘扬佛法的宏愿,风尘仆仆,一路从西域来到中原。洛阳那时是西晋的都城,他就在那里歇下脚来,宣传佛教。当他看到石勒的部下在征伐中大肆滥杀,便想以佛法感化石勒,制止其杀戮。于是,他通过石勒手下的大将郭黑略,想办法接近石勒,取得了他的信任,让其逐渐接受了佛教思想,并一度担任石勒的“军师”。
石勒称帝后,还非常信任佛图澄,尊称他为“大和尚”,还把自己的孩子“舍”给他所在的寺院,让他们每天吃住在寺庙,系统地接受佛教文化的教育。
在石勒的提倡下,佛法大行于天下,石勒也因此称为中华佛教史上第一个礼佛的君王、第一个建正规佛寺的君王。石勒之后的后赵皇帝石虎也笃信佛教,说“我是胡人,当信胡神。”石虎也尊佛图澄为“大和尚”。
有了石勒、石虎两代帝王的信任和支持,佛图澄的心愿也得以完成,短短几十年内,“所经州郡,建立佛寺,共893所。”
对于皇帝的家乡榆社,佛图澄自然更加不遗余力地推广佛教文化。榆社史志办主任任林峰说,志书《上党国记》中有记载,“赵建武元年(335年),澄(佛图澄)奉虎(石虎)命,携徒道安诣榆(今榆社县城),适城空空也,唯衙门独处。澄喜极,曰:‘吾之志逞也。’”于是,佛图澄请来县宰督办修建寺庙,“集民夫三千,且将半城花插佛地,留半城为民居,凡五载毕,城内外立寺庙316所。僧尼二千,澄与徒传教说法。”由此可见,佛图澄耗费5年时间,在榆社县城建立寺庙316所,榆社一半的土地上都有了寺庙。“正因为此,榆社当时被称为‘小西天’。即使在今天,榆社的每座山上都能找到古寺庙的遗址。”任林峰说。至此,佛教,以绝对优势,在榆社生根发芽。
而后到了北魏时,推崇佛教的孝文帝要迁都,把皇室贵族从平城(今山西大同)迁到洛阳。而古榆社,是平城到洛阳的交通要道之一,是迁都路上最为便利的一条道路。在北魏政治集团大迁徙的过程中,笃信佛教的王公贵族和大批佛教石刻艺术工匠们途经榆社,在此歇息、停留,留下了佛教的思想文化,也留下了精湛的佛教石刻、雕塑、建筑、绘画等艺术技能。
榆社县作协主席李旭清在其著作《沧桑榆社》中这样表述:“榆社是我国早期佛教文化的博览室,是我国早中期佛教石刻艺术的过渡带。”不无道理。
榆社舍利塔天下第十八塔
虽然榆社有丰富的佛教文化遗存,但经过历史上几次灭佛运动、战争、“文革”、自然灾害等,许多佛教建筑和石刻被毁坏得所剩无几。李旭清告诉记者,“有些只剩下断壁残垣,比如金厢寺、安国寺、弥陀寺,有些极为珍贵的建筑甚至已荡然无存,比如大同寺舍利塔。”他非常遗憾地说,“能够保留下来的,估计不及原来的10%。”
最让人痛心的,莫过于大同寺舍利塔的消亡。
相传,在佛教发源地古印度阿育王时代,曾将佛祖释迦牟尼的佛骨舍利子分成88400份,派使者分送到世界各地建塔供奉,弘扬佛法。世界各地也因此有了8万多座佛舍利塔。据说,传入我国境内的舍利子有19枚(又说21枚)。
佛教百科全书唐代《法苑珠林&敬塔篇》详细记载了这19座舍利塔的所在地、建造时间。其中,榆社县大同寺舍利塔赫然在列,名列第十八位。大同寺舍利塔也因此被称为“天下第十八塔”。
李旭清自豪地说,“佛祖舍利是佛教顶级圣物,全中国一共19枚,山西占了5枚,而榆社竟然就是其中之一!”
遗憾的是,大同寺连同舍利塔已永远消失。据一些专家推测,早在清代早期,舍利塔就已坍塌,但大同寺还在。到后来,大同寺不知因何也被毁,所幸清道光年间被重修,连舍利塔也一起被修复。光绪版《榆社县志》对此有记载:“大同寺,在城外东南,元时改建。后寺全毁,仅保存石佛像。道光八年,邑令陈维屏督同绅董王席宾、李天乙等重建,中殿即舍利塔。”但到了光绪年间,大同寺的一部分又被洪水冲毁,剩余部分则在抗日战争时期毁于日军飞机轰炸。李旭清接触过一些老人,他们都有“大寺圪垯”(大同寺遗址)的记忆,都说曾经见过那座舍利塔。
2001年,榆社县文物工作者在大同寺旧址上发掘出140多尊佛教石刻造像。从佛像题记上看,雕造年代跨越了北齐、北周、隋、唐等4个朝代。
而今,这里已被改建为县公安局宿舍区,大同寺舍利塔也逐渐淡出人们的记忆。但对于“佛舍利今何在”话题的关注,一直没有停止过。文物专家分析认为,佛舍利应该还深藏于塔遗址下的地宫之中。
山西省及榆社县文物、文化部门诸多专家都对此深表期待,他们说,如果有一天,榆社舍利塔的地宫重见天日,那么其中安奉的文物及其历史文化价值,恐怕不亚于陕西法门寺。
佛教石刻造像叙述往日佛国盛况
榆社有位90多岁的郝福瑞老人,曾凭记忆手绘了一幅1937年前榆社县城图。根据这幅图上的标注,我们依稀可以瞥见旧日榆社佛文化繁盛的景象。而今,很多寺庙虽已不见踪迹,连遗址都难寻觅,所幸当年还保留下些许石刻造像,如今可去榆社博物馆细细赏析。
早期的榆社佛教石刻,多为“凿山石壁,开窑造像”,其风格粗犷、威严、雄健,神态冷漠、不苟言笑。但北魏及北齐时期的石刻造像则多了些“人”的平和。到隋唐时,榆社石刻造像的审美风格更趋本土化,由神情冰冷转向慈祥和蔼。这样的佛教石刻造像,或坐或立于田野之中,让辛苦了一天的百姓抬头可见,似乎在心头飘过一缕清风,真可谓榆社人的一大幸事。
但不幸的是,有些珍贵的石刻造像却流散在外。
“南村站佛高4.6米,头发呈波纹状,面部丰满圆润,眉如弯月,目光慈祥,眼睛半睁半合,俯视着脚下的芸芸众生。嘴边微露笑意,显示出内心的平和与安宁……”介绍资料这样说。
就是这尊佛像,榆社县文物局局长、博物馆馆长王太明有一年去台湾参观访问,遇到一个老兵,自称老家是榆社云竹镇南村人。看到老家来人了,他激动地说,“记得我小时候常见村外站着一尊大佛,可前段时间,我在台湾故宫博物院看到了它。奇怪啊,它明明是站在我们村口的,我那时天天都见,怎么跑到台湾了?”
为了避免这样的事再次发生,并保存、保管好石刻文物,文物管理部门已将石刻造像一个个从山风野岭中拔起,移到博物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