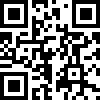拥有1500多年历史的洛阳龙门石窟,是享誉海内外的中国古代石刻艺术宝库和世界文化遗产。站在龙门石窟前,每一个人都会被其壮观华美深深震撼,同时,又不能不为满目的伤痕疮疤而扼腕叹息。
这里共有1300多个石窟、97000余尊佛像,从最大的高达17.14米的卢舍那大佛,到最小仅有2厘米的佛造像,没有一个是完整的!
1500多年间,龙门石窟经受着大自然的风霜侵蚀,遭历了唐代的灭佛运动,但最大的劫难来自近代。从清末民初到新中国成立前的几十年中,西方文化强盗勾结利欲熏心的文物贩子,大肆盗凿龙门石窟,佛头被砍下,雕像被肢解,浮雕被凿碎……越是精美的石刻艺术品,越会被当做劫掠的目标。它们被简单粗暴地从石窟中凿下,偷运境外,流向了欧美和日本等地。
其中最令人痛心的,就是开凿于北魏时期的浮雕——“帝后礼佛图”。它本是龙门石窟石刻艺术宝库中最瑰丽的珍宝,它被盗凿的过程,也能够还原出那段历史中国宝流失的典型路径。
“一座尚未开放的万神殿”
从洛阳市区驱车向南12公里,远远就可以看到伊河两岸相对而立的龙门山和香山,两山相望,就像一座天然的门阙。春秋战国时期,这里被称为“伊阙”。隋代,洛阳被定为东都,“伊阙”成了天子门户,改名“龙门”。
龙门石窟就开凿于山水相依的峭壁间,始凿于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前后。
北魏孝文帝是在中国历史中留下重要一笔的皇帝。南北朝初期,鲜卑族政权北魏一统北方。孝文帝亲政,革俗汉化,强令鲜卑人改用汉姓,改穿汉服,改说汉话,以雷霆万钧的手段加速了民族大融合,也深刻影响了汉文明的发展。孝文帝深感国都偏于北方不利于统治,于是在公元493年将国都从平城(今山西大同)迁于洛阳,同时拉开了大规模营建龙门石窟的序幕。
正是在南北朝时期,佛教在中国开始迅速发展。诗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在北朝,则盛行开凿石窟。比龙门石窟略早的云冈石窟,也是始凿于北魏。后来北魏迁都洛阳,龙门石窟就成了北魏皇家贵族发愿造像最集中的地方,具有浓厚的国家宗教色彩。
龙门石窟中形制最大的卢舍那大佛作于唐高宗时期,至今仍是最能代表龙门石窟的佛造像。北魏没有盛唐气象,营造的石窟相对较少,但一来年代更久远,历史信息深厚;二来自身艺术风格浓郁,北魏石窟同样蔚为大观。
中央民族大学考古文博系副教授刘连香告诉记者,北魏佛像与唐代佛像在艺术风格上截然不同。北魏晚期风行的“秀骨轻像”,佛像显得俊逸修长,不像唐代佛像那样体态丰盈。
古阳洞开凿于公元493年,是龙门石窟开凿最早的一个洞窟,但若论艺术水平,则要首推北魏迁都洛阳后开凿的宾阳洞。
公元499年,迁都仅仅6年,年仅32岁的北魏孝文帝去世。次年,其子北魏宣武帝为父亲做功德,开始营造宾阳洞石窟。“宾阳”意为迎接初升的太阳。
宾阳洞前后建造了24年,富丽堂皇的景象为龙门众石窟之冠。不过,宾阳洞的营建却十分坎坷。史书记载,宾阳洞施工五年才“斩山二十三尺”。宣武帝非常不满,将最初的工程主持人换掉,可是新上任的主持人没几年便去世了。宣武帝只好把宾阳洞的工程交给宦官刘腾。刘腾觉得一座洞窟不足以彰显君威,奏请宣武帝在南北加造两座洞窟。于是,最初的宾阳洞便成了宾阳中洞。
公元515年,宣武帝驾崩,7岁的孝明帝即位,胡太后临朝称制。刘腾联合领军元叉,以太后“淫乱肆情”为由,发动宫廷政变,幽禁了孝明帝和胡太后。4年后,刘腾病死,胡太后重返朝堂。
经过几次三番你死我活的宫廷斗争,胡太后再次临朝,自然没有什么心情继续整治对手所主持的宾阳洞。此时,宾阳三洞只完成了中洞,工程就此废止。理想中的辉煌工程虽然没有完全实现,但是宾阳中洞的石刻已足以震撼人心。
宾阳中洞深12米,宽10.90米,高9.3米,洞内正壁中央供奉着释迦牟尼跏趺坐。窟口内壁两侧各有一个上下四层的浮雕,最上层是“维摩变”;第二层是佛本生故事;第三层就是着名的帝后礼佛图;最下一层是“十神王”浮雕像。
刘连香告诉记者,在龙门石窟的北魏石刻中,宾阳中洞的帝后礼佛图称得上等级最高、艺术水平最高的作品,甚至可称龙门之冠。
帝后礼佛图是两幅浮雕的合称。图分左右,左壁为北魏孝文帝礼佛图,右为文昭皇后礼佛图,分别刻画了孝文帝和文昭皇后带领侍从列队礼佛的场景。两幅浮雕人物密集,顾盼神飞,浑然一体,堪称中国艺术史上的杰作。浮雕中的衣冠仪仗,忠实记录了北魏孝文帝强行推动汉化后的服饰特征,极具史学价值。
北魏没有完成的宾阳南、北二洞,一百多年后在唐太宗时期得以完工。值得一提的是,宾阳南洞的营造还记录了一段唐代皇位之争的历史。
唐太宗时期,太子承乾因荒淫被废,众皇子觊觎皇位蠢蠢欲动,其中表现最为积极的是皇四子李泰。李泰与承乾一样都是长孙皇后所生。长孙皇后病逝,李世民极为悲恸,李泰便奏请开窟造像纪念母后。
然而,李泰营造石窟并非为了尽孝,而是为了给自己积累政治资本。工程不求精益求精,只要求快。于是,他选中了半拉子工程——宾阳南、北洞。宾阳南、北洞的洞窟已经造好,只要稍加修缮再雕刻几个佛像就万事大吉了。不过,这样敷衍的工程与宾阳中洞自然不可同日而语。盛唐之时完工的宾阳南、北洞,无论工艺水平还是艺术价值,都逊色北魏的宾阳中洞不少。也许,正是由于投机取巧,李泰最终失去了父亲的欢心,在夺嫡中败下阵来。
此后数百年间,龙门石窟不断地被后代王朝修复、续作,历经千年时光,伊河两边的峭壁上共开凿了1300多个石窟。时至今日,龙门石窟共存窟龛2345个,题记和碑刻3600余品,佛塔50余座,造像9.7万余尊。无论规模,还是艺术成就,都堪称中国石窟艺术的巅峰。
伊河静静地流淌,倒映着河岸的龙门山、香山,以及山体峭壁上的慢慢伸展开来的龙门石窟。这里从唐代就是着名景观,白居易曾记:“洛都四郊,山水之胜,龙门首焉。”世代生活于此的人们,早已习惯了龙门石窟的存在,它是风景,也是求神拜佛之所。
直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到这里,把另外一种价值添加到了龙门石窟之上。灾祸由此而起。
第一个将龙门石窟介绍给世界的外国人是日本学者冈仓天心。
1893年,在中国游历的冈仓天心偶然发现了龙门石窟。站在巨大的佛像前,钻进华美的石窟里,冈仓天心彻底被雄伟瑰丽的景观震撼了。他在日记中赞叹:“龙门石窟自身就是一座博物馆,有上万座石像,有唐代的作品,甚至还有宋代的作品,制作年代也非常可信,其重要性无法估量,多么美丽的地方!”
在中国游历后,冈仓天心回到日本,用宾阳洞的照片制成幻灯片,举办了讲座。龙门石窟很快声名远播。此后,法国汉学家爱德华·沙畹、美国收藏家查尔斯·朗·弗利尔、日本学者关野贞等等纷至沓来。这些人,有为历史文化或是风景而来的学者、旅行家、探险家,当然也有为了文物而来的收藏家,还有干脆就是为了金钱而来的古董商乃至文物盗贼……有些人则是几种身份兼而有之。
冈仓天心的学生——美国人兰登·华尔纳,就是其中之一。
兰登·华尔纳1881年出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1899年,他进入哈佛大学学习。1906年,他留学日本,师从冈仓天心,专攻佛教美术。他为哈佛大学开创了东方艺术课程,也曾在几家美国博物馆担任高级职务。
然而,对中国来说,兰登·华尔纳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文物大盗。
1923年,华尔纳潜入敦煌莫高窟,剥离莫高窟唐代壁画精品10余幅,并盗走第328窟彩塑供养菩萨像等。由于他揭取壁画的方式极其简单、原始、粗暴,壁画完全破碎,遭到了不可逆转的破坏。至今,人们仍能在一些洞窟中看到壁画被剥离后触目惊心的现场。
在去敦煌前,华尔纳就到过龙门石窟。甚至在去龙门石窟之前,华尔纳就已经深深为其吸引,而且最关注的就是帝后礼佛图。
华尔纳收集了冈仓天心、沙畹、弗利尔等人拍摄的龙门石窟照片,并挑出帝后礼佛图的照片寄给波士顿美术馆,在信中写道:
你可以看到古代中国雕塑在全盛时期的样子。请留意那些礼佛人物——它们的构图与罗马万神庙的装饰雕刻一样好,至于那些浮雕的线条,我认为它们也毫不逊色……先生(冈仓天心)认为它们非常重要。西方应该能够接触到那座顶级中国雕塑宝库,那是一座尚未开放的万神殿,堪称整座雅典卫城,等待着人们去学习研究。
龙门石窟这座“尚未开放的万神殿”,等到的却不是来学习研究的人。
龙门乱象
清末民初,随着冈仓天心、沙畹等学者关于龙门石窟的研究专着的不断推出,世界各地贪婪的目光盯上了龙门。
沙畹所着《华北考古图录》发表于1909年,其中的照片刺激了西方的收藏者。当时即有一位名叫斯坦利·亚伯的英国公爵撰文评论:法国人的学术着作“无意中提供了带照片的目录,外国买家可借此在公开市场追求,或有时候‘特别预订’所挑选作品,即告诉他们在中国的代理,他们对获得龙门石窟哪些东西感兴趣”。
1911年,一般被认为是龙门石窟遭受大规模盗凿的肇始之年。《龙门石窟盗凿史》一文的作者、洛阳学者赵振华告诉记者,龙门石窟被人为毁坏最严重的时期几乎可以贯穿20世纪上半叶。
1911年,考古学家罗振玉派弟弟罗振常到河南收购古董。罗振常在日记中记录下当时龙门石窟被毁的情况:“顾小窟往往空洞无像,大龛诸佛亦多残损,每有失其首者。”他还听当地百姓说,来龙门石窟游览的外国人很多,他们看上哪个佛像就花钱雇工匠往下凿。地方官根本不管,寺庙和尚监守自盗,游客随便盗凿。他不由得感叹:“此名迹将日见颓废,是可太息者也。”
内外勾结,破坏龙门石窟的情况,甚至连英国《泰晤士报》都报道了。1914年,《泰晤士报》写道:
巨大的人物浮雕……被盗贼肆意切割、锯断或摔成碎块,以便运往北京,并出售给欧洲古董商。收藏家或博物馆的代表,迫不及待地买下他们。那些人会对参与走私踌躇迟疑。但是他们反驳道,既然那些战利品已落入他们手中,他们至少有责任为其提供一处值得停留的地方。竞争在增长,价格在飙升,破坏的动机进一步受到刺激,变得日益高涨。
民国初年,龙门石窟遭受如此惨烈的人为破坏,民国政府是不是完全熟视无睹,撒手不管呢?赵振华认为,这样说也有失偏颇。
1914年,北洋政府内务部致河南民政长训令,要求省里派专员,会同当地官员到龙门石窟调查,将龙门石窟所有佛像石刻登记在册,并责成附近寺庙僧侣管理,酌情给予津贴。
洛阳县知事曾炳章用了两年时间,对龙门石窟进行了调查。据他考察当年龙门石窟有大佛476尊,其中有破损的达180尊;小佛89375尊,其中有破损的达7275尊。当然,这还是1910年代龙门石窟的状况。赵振华认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是龙门石窟有史以来遭受盗凿最严重的时期。也就是说,在曾炳章调查报告出炉后的20年,又有数不清的石刻珍品遭到了破坏。
1916年,河南省出台了首例关于龙门石窟的保护法案——《保护龙门山石佛规条》。1930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了《古物保护法》,同时成立了“中央古物保护委员会”。河南省政府也派军队驻扎龙门,但是由于土匪太过猖獗,官方的保护总显得力不从心。
1914年,已经关注龙门石窟多年的华尔纳,终于得到机会亲赴龙门考察。他发现那里治安状况十分糟糕,甚至连一个晚上都住不下去。洛阳的治安官警告他说,仅在龙门石窟外就有1000名盗贼。军队每晚都出动,与盗贼发生冲突。就在他抵达龙门的两天前,军队刚刚与盗匪进行了一场激战,一举歼灭了100多名匪徒。
华尔纳到达龙门石窟时,看到墙上挂着土匪的首级。“邪恶的乌鸦在每个脑袋上啄食,在横跨洞窟、挂着被砍下头颅的横木间栖息。石窟墙壁的外面也有一些尸体。”
然而,正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来自西方的高额“悬赏”,让盗凿龙门石窟的不法分子源源不断,官方的介入并没有使盗凿龙门的状况得到丝毫缓解。倪锡英所着《洛阳游记》一书中,就专门记录了1933年他和李可染受中国社会教育社理事会派遣到龙门石窟考察时看到的一幕:
每一年,各国的游历者到龙门去拜访的总在几百以上,他们每次来都花了重金向乡人购买石佛的头,带回去作为名贵的艺术装饰品。帝国主义资本的势力居然延展到洛阳,龙门山窟里的石佛被带到外洋各国去了,这非但是石佛的不幸,同时也是整个大胜迹的不幸。
第二年,受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到龙门石窟考察的地质学家袁同礼,看到了同样的景象。来龙门游览的外国人花钱找村民盗凿佛像。其中宾阳洞、八仙洞、千佛洞等洞窟被毁坏的情况最为严重。宾阳洞中四个佛像头颅被击落,洞内外龛像有被砍头的,也有全身被盗的。
袁同礼在报告中称,龙门石窟被疯狂盗凿的情况,以1930年以后的三年最为炽烈。“龙门之南的外凹村,许多石匠都以盗凿龙门石像为业。他们勾结土匪,夜里携带云梯、手电筒到洞窟中盗凿。很快,这些被砍下的佛头就会出现在北京的文物市场上。”
这些荷枪实弹、明火执仗的盗匪背后,无不站着一个财力雄厚的外国金主。
华尔纳是最早从照片中发现龙门石窟价值的人之一,也很快意识到这些照片正被欧美收藏家用作“收购目录”。
1913年,他去欧洲旅行,顺便访问了巴黎的赛努奇博物馆。华尔纳向自己当时的导师和雇主查尔斯·朗·弗利尔报告,提到了赛努奇博物馆最近取自中国石窟的十几尊雕塑。华尔纳指出,欧洲的古董商们已向他们在中国的代理标注了龙门石窟的照片。代理们正根据订货,委托当地的石匠偷盗雕像。
在信中,华尔纳还表示担心自己的有关中国照片的出版物也会带来同样结果。“那种事情,将会极度伤害我的良心。”华尔纳的这番表态可以说是“鳄鱼的眼泪”,因为他自己很快就成了这样一个“金主”,或者说是“金主”代理人。
破碎的皇后礼佛图
上世纪30年代,华尔纳已经离开中国,在剑桥谋得教职。不过他仍对中国散落各地的文物珍品念念不忘。此时,他找到了一个回报颇为丰厚的副业——为堪萨斯城正在修建的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提供藏品征集的咨询服务。中国是他提供的最丰富的藏品“征集”地。
由于他远在剑桥,不能亲自到中国,于是他将自己的学生——劳伦斯·史克曼推荐给博物馆。
史克曼1930年毕业于哈佛大学。在哈佛上学时,史克曼选修了华尔纳的课,并得到了老师的赏识。1931年,史克曼拿到哈佛燕京学社的奖学金。这些钱足够他在北京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
为了带学生上道儿,华尔纳还亲自来北京,与史克曼住了一段时间。离开中国时,华尔纳把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提供给他的5000美元征集费留给了史克曼。后来,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每月固定支付给史克曼100美元薪酬,让他专职物色文物。100美元在当时是笔不菲的收入。史克曼拿到这笔薪水后,更加废寝忘食地帮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寻找“猎物”。
史克曼在北京的日子里,搜罗了大量古董。当时也住在北京的英国贵族哈罗德·艾克敦在《一位唯美主义者的回忆录》中写道,一天中的最好时光,就是看到史克曼怀抱珍宝走进房间。“史克曼抱着中国古董的样子,就仿佛怀抱着一个沉睡的公主。”
史克曼很信服德国古董商奥托·伯查德。伯查德经常带史克曼逡巡于北京的古玩行中。在伯查德的带领下,史克曼穿过摆满各种廉价古董的前厅,来到古董商们不轻易示人的后院,只有在那里,才会出现稀世珍宝。
史克曼学习能力很强,很快就在北京的古玩行里混得如鱼得水。他与龙门石窟的第一次相遇是在1931年秋天。
第一次来到龙门的史克曼,完全被龙门精美的石刻征服了,他在龙门停留了一个星期,做了大量笔记。在宾阳洞中,他看到了还很完好的帝后礼佛图,并让工匠为他制作了帝后礼佛图的拓片。
1933年,当史克曼再一次来到龙门石窟时,发现宾阳洞中文昭皇后礼佛图上几个人物的头部,以及大部分浮雕,已经不翼而飞。
不久,他听说伯查德买到了文昭皇后礼佛图中的两个女性头像。他在给华尔纳的信中说,越来越多的浮雕碎块流入市场,他与伯查德商量将尽其所能收集所有碎块。
虽然史克曼一直公开声称,自己收集文昭皇后礼佛图的碎块是为了保护“那尊北魏典范雕塑的安全”,但恐怕他自己也说不清楚,哪些碎块是早就被凿下来的,哪些是因为他的收购而被有目的地凿下来的。
晚年,史克曼在回忆录中写道:“就我个人而言,如果它(文昭皇后礼佛图)从未离开宾阳洞,我会为此付出我的所有。”从这段表白中,不难看出他对龙门石窟遭受的破坏怀有愧疚之意。不过,当年为那些盗凿龙门石窟的行径提供“动力”时,史克曼可是没有丝毫犹豫。
史克曼在给朋友的信中这样描述自己收集碎块的过程:
从这里到那里,从这家店到那家店,从开封到郑州,是的,包括上海,我一块接一块地收集,这里收半个脑袋,那里收一条袖子;从夏先生手里收一只手,成百上千的小碎块……不管怎样,早期中国雕塑最伟大的单件浮雕被组合在一起……我们花了3个月时间,把它们一块块拼接起来,像一群男孩子整天坐着,试试这块,试试那块,哪块该放在哪里,合不合适?那是一只眼睛,还是一条服饰花边?
将文昭皇后礼佛图拼好后,史克曼用3个大箱子将它运送到美国,入藏堪萨斯城的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中。
被敲成碎块的浮雕,怎么可能被一一找回,又拼回原样?正在研究文昭皇后礼佛图的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编辑部副主任霍宏伟,向记者道出了自己的疑惑。在霍宏伟看来,现在保存在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中的文昭皇后礼佛图,太完美了,几乎看不出修复的痕迹。龙门石窟礼佛图题材的浮雕大多为浅浮雕,以当时石匠的手艺不可能凿下整片的残块,更不可能将它们修复如初。虽然还没有可靠的证据,但霍宏伟怀疑,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中的文昭皇后礼佛图不完全是真品。
据《谁在收藏中国》一书中的记载,当年史克曼自己也曾有过类似的怀疑。当他把修复好的文昭皇后礼佛图送往美国后,他又在北京的文物市场发现了类似的残块,有些头像和衣服褶皱跟他收集到的一模一样。
内外勾结
得知文昭皇后礼佛图入藏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的消息,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东方部主任普爱伦坐不住了,他立即投身到争夺北魏孝文帝礼佛图的竞争中。
普爱伦是一个中国通。上世纪20年代,他在北京有一段极为惬意的生活。他租了一个四合院,雇了一名中国厨师、一名黄包车夫,还有一名年轻的中国学者做助手。每天早上,一名老先生来教他读3个小时的《孟子》。晚上,他和助手一起读读报纸,侃侃大山。周末他或在城里逛逛寺庙,或去西山玩一圈,滋润之极。
普爱伦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
我在北京小胡同、戏院、公园、茶馆和中国人家里停留的每一分钟,都为我提供了更好地理解这个国家的途径,使我更有理由判定:这是宋代绘画,那是北魏石刻。我爱中国人。有时候,我也会使他们痛苦不堪,但是我依然爱他们。我愿在自己的墓碑上刻上3米高的大字:“世上有两个最伟大民族:希腊人和中国人。”
普爱伦对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表白,已达到肉麻的地步。然而,他所说的话中,大概只有“我会使他们痛苦不堪”这一句是真的。
上世纪30年代,荣升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东方部主任的普爱伦要大干一场。他发誓要“构建与纽约这座城市和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规模相匹配的收藏。”这时,他盯上了龙门石窟。
再次来到北京后,普爱伦找到琉璃厂古董商岳彬。
岳彬是琉璃厂的大古董商。1910年,14岁的岳彬离开通州张家湾,跟着在鬼市卖旧货的朱二当学徒。20年后,他已经成了名震琉璃厂的古董巨商。可以说是一个神话般的人物。
岳彬是怎么发迹的呢?据琉璃厂老行家陈重远先生回忆,岳彬最早发迹就是做外国人的买卖。
1914年,岳彬搬到狗尾巴胡同兴隆店,开始自己夹包做生意。岳彬嘴甜,会来事儿,深得兴隆店瑞记古玩店掌柜的白瑞斋喜爱。于是,白瑞斋开始教岳彬跟外国人做买卖的诀窍。久而久之,美国人爱买青铜器、钧窑瓷器;法国人爱买漆器、景泰蓝;日本人爱买古玉、龙泉瓷器;英国人、德国人要考古价值高的东西……都被岳彬摸得一清二楚。
1917年,岳彬把一件明代瓷器当做宋瓷卖给了曾经担任过法国驻华公使的魏武达,挣到了第一桶金。此后,岳彬的生意越做越大。1928年,他在大栅栏炭儿胡同买下一座有东西两个跨院的大房子,开了古玩铺——彬记。岳彬的古玩生意涉猎很广,石刻只是其中之一。
岳彬的徒弟董祖耀曾向陈重远回忆,上世纪30年代,一个美国人经常光顾彬记,他们都称他为“布老爷”,他就是普爱伦。“布老爷”曾经拿着北魏孝文帝礼佛图的照片向岳彬订货,要他想办法凿下来。为此,普爱伦出价1.4万大洋,限期五年。
于是,岳彬找到洛阳当地的古董商马龙图合作。马龙图出面联络龙门地面儿的保甲长和土匪,凿下了北魏孝文帝礼佛图。
土匪们没敢把北魏孝文帝礼佛图的碎块直接送到北京,而是运到了保定。岳彬打发他的大徒弟丁兆凯特意跑到保定,把碎块从保定火车站接到北京。
据丁兆凯和另一个徒弟王福祥后来透露,等几麻袋碎石头运到岳彬家,他就傻眼了。北魏孝文帝礼佛图被盗贼们凿得太碎了,根本拼不上。他们找来修复古铜的大师张济卿帮忙修复,几麻袋碎石头摆了彬记西院一地,找碴口拼对,可就是拼不上。最后没辙,他们按照普爱伦提供的照片,仿造了一个,交差了事。
按丁兆凯所说,普爱伦买到的是一个假的北魏孝文帝礼佛图。事实果真如此吗?
一纸合同揭阴谋
经岳彬之手流出国门的国宝不计其数。新中国成立后,他自知罪孽深重,人民政府也不可能再让他干倒卖文物的勾当。于是,他把四个徒弟和一位管账先生叫到一起,哭着说:“看来我这买卖就开到这儿了,往后谁还买古玩?我不耽误你们,大伙儿另找事做去吧!”然后,他给每人发了一些遣散费,曾经红极一时的彬记古玩铺就算散伙了。
岳彬本以为自己可以凭着多年攒下的家业颐养天年。可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1952年初,国家在全国工商业中开展了“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和反盗窃经济情报”的运动,也就是俗称的“五反运动”。
岳彬认为自己买卖也关张了,又没有行贿和偷税漏税,“五反运动”跟他关系不大。于是,工作人员来查账时,他就大大方方地把陈年老账拿出来。
没想到一查账,他就漏了老底儿。工作人员竟然从彬记20世纪30年代初的老账里查出了岳彬同普爱伦交易北魏孝文帝礼佛图的合同。
合同中记载:
立合同人普爱伦、彬记。今普君买到彬记石头平纹人围屏像拾玖件,议定价洋一万四千元。该约立之日为第一期,普君当即由彬记取走平像人头六件,作价洋四千元,该款彬记刻已收到。至第二期,彬记应再交普君十三件之头。如彬记能可一次交齐,普君则再付彬记价款六千。如是,人头分二次交齐,而此四千价款,亦分二期,每期二千。以上之货,统计价洋一万四千元。
从这纸合同可以看出,1934年立合同时,岳彬已经给普爱伦6个人物头像,普爱伦为此支付了4000大洋,第二期岳彬应该再给普爱伦13个头像。
合同白纸黑字写得明明白白,是普爱伦向岳彬订货,岳彬联合当地古董商、土匪再去洞窟中盗凿的。然而,1944年普爱伦出版的着作《中国雕塑》一书,却把自己撇得干干净净。普爱伦写道:
在1933年和1934年,来自于这一特殊石窟中男、女供养人浮雕上的头像、衣纹服饰及其他残片开始出现在北京的市场上。它们是这样被凿下来的:在龙门石窟附近河流对岸可以看到一座小村庄,夜间,村民蹚过腋窝深的河水,将浮雕表面凿成碎片。他们把碎片带到郑州,被北京的代理商买走。在北京,这些碎片被重新粘接拼合,并根据照片和拓本进行了精心复制。你将会发现属于龙门男、女供养人浮雕的头像广泛散布于欧洲、英格兰、日本各地,而他们大部分完全是赝品。美国的两座博物馆已经购买而挽救了这两块浮雕——女供养人浮雕残块在堪萨斯城的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展览,大都会博物馆买了男供养人浮雕碎片。
这段叙述有真有假。普爱伦把自己装扮为这件稀世珍宝的拯救者,自然是假的。不过,文字中提供了另一部分相当可信的信息:文物交易黑市里,流传着大量赝品帝后礼佛图残片。
前文提到,岳彬的徒弟丁兆凯和王福祥说岳彬从土匪手中拿到两麻袋碎石头,摆了一院子愣是对不上碴儿,迫不得已,伪造了一套北魏孝文帝礼佛图给了普爱伦。
王福祥还曾在回忆中补充细节,后来普爱伦发现北魏孝文帝礼佛图是岳彬伪造的,也没有按合同付余款。王福祥还抱怨:“我们掌柜的做这号买卖没赚多少钱,加工复制花钱不少,劳神费力还进了监牢。”
岳彬后来被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1959年死于狱中。
上世纪60年代曾任文化部文物局局长的王冶秋在《琉璃厂史话》中记载,文物工作者不但发现了这份合同,而且还从岳彬家抄出来两大箱没有拼接上的浮雕碎块。这些碎块都已经归还给了龙门石窟,却再也拼不全北魏孝文帝礼佛图。
1965年11月,龙门文物保管所找到了当年参与盗凿北魏孝文帝礼佛图的石匠王喜光、王水和王惠成了解情况。三人的回忆让更多盗凿细节浮出水面。
据他们回忆,1930年至1935年间,洛阳东关古董商马龙图勾结村保长王梦林等人,胁迫石匠深夜潜入宾阳洞。为了怕惊动龙门当地群众,还有荷枪实弹的土匪给他们站岗放哨。
王喜光说,他们主要凿宾阳中洞北边下面的身子(即北魏孝文帝礼佛图)。照片在马龙图那里放着,打一回看一回照片,按打的多少付钱。他们把打下来的碎块,陆续送到洛阳城东关马龙图的店里。怕人查问,他们特意在碎石上面盖一层石灰,谎称是进城卖石灰的。
石匠们反映,宾阳洞的石头是火硝石,打起来直冒火星,非常费劲,光宾阳洞的北魏孝文帝礼佛图就打了两三年。
存续1400多年的北魏石刻,就这样一片一片被硬生生地凿下来,粉身碎骨,再也不复当年的模样。
普爱伦买到的北魏孝文帝礼佛图真假且不论,北魏孝文帝礼佛图因为他的“收购”而被破坏是无可辩驳的事实。他正是整个盗凿生意的幕后主使,不折不扣的文物大盗。
永远拼不上的“中国拼图”
普爱伦买下的北魏孝文帝礼佛图,现在还被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收藏着。
2011年,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做访问学者的刘连香,第一次在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二楼的中国艺术展厅看到了修复后的北魏孝文帝礼佛图。它就在最显眼的山西广胜寺巨幅壁画对面,被镶在一个展板上。
由于曾在洛阳工作,刘连香逛博物馆时特别关注洛阳的文物。“看到它支离破碎的样子,我心里特别难受。”刘连香说。
作为一名专业考古人士,刘连香除了难过,还觉得有些奇怪。她记得,1909年沙畹拍摄的北魏孝文帝礼佛图照片中,可以清晰地看出浮雕位于东壁和北壁,在东北拐角处有一个明显的转折。为了处理这个拐角,工匠们在这里别具匠心地雕刻了一棵菩提树。菩提树左侧,也就是洞窟北壁上又有8个人物。他们与东壁上的人物在方向、形态上完全一致,是礼佛队列的一部分。
大都会展出的北魏孝文帝礼佛图被镶在一块展板上,别说拐角,连菩提树也没了。为了让东壁和北壁上的人物联成一体,修复人员还故意在菩提树的位置多做出许多人物的衣纹褶皱。
刘连香告诉记者,这种情况同样出现在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展出的“皇后礼佛图”中。博物馆仅修复了东壁上的浮雕,而没有修复南壁上的两个羽葆和众多人物。
同时,刘连香注意到,大都会博物馆展出的北魏孝文帝礼佛图上有许多莫名其妙的部分。浮雕的人物头像都独立于身体之外,大多跟下面的身体对不上碴儿。有些雕刻的人物头像相对完整,可是呈现出一种奇怪的黑色,与浮雕整体色调极不和谐。
由于北魏孝文帝礼佛图不是以人物大小来表现身份高低的,只能通过人物的神态、布局和冠饰来分辨哪个是核心人物北魏孝文帝。刘连香认为,负责盗凿的石匠,乃至岳彬本人,很可能对浮雕中的人物关系一知半解。因此,在盗凿过程中魏孝文帝所戴的冕旒被破坏了。如今展出的浮雕中,北魏孝文帝的衮冕顶部没了,垂下的缨带也没有了。看起来,北魏孝文帝就像戴了一顶普通官员戴的进贤冠。
刘连香告诉记者,正是由于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展出的北魏孝文帝礼佛图错误百出,有人甚至认为它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赝品。不过刘连香认为,大都会展出的浮雕中,人物头部大部分都是真品。由于原浮雕中人物头部分布疏朗,凿的时候比较好下手,石匠应该是先将人头凿下来的。这个推断与岳彬手里的合同也相符。普爱伦第一批先从岳彬手里拿走了6个头像。至于人物身体和服装部分,有多少是真品修复的,有多少是伪造的,就不好说了。
在龙门历经了1400多年风风雨雨的帝后礼佛图,就这样在国际大盗和不肖子孙的双重戕害下支离破碎。无论再用多么高超的修复技术,再用多么先进的科技手段,也无法弥合浮雕上的裂痕,两件艺术珍品再不复当年的辉煌。如今,人们在这两件艺术品上已经看不出多少美感,看到的更多的是人们的私心、贪欲与邪恶。